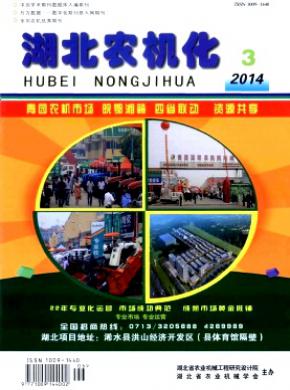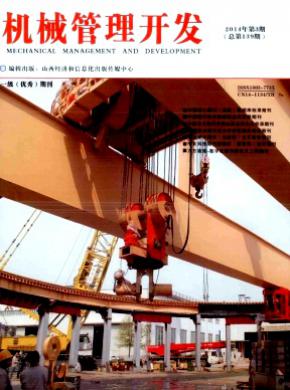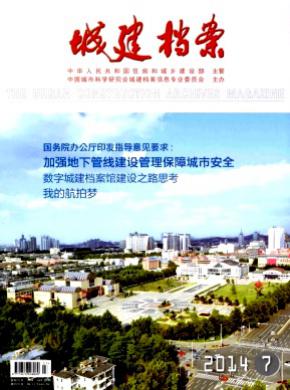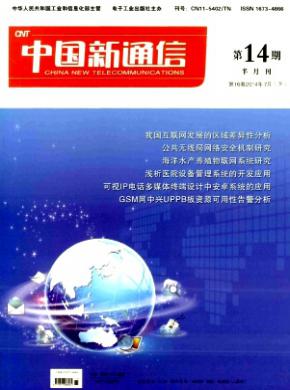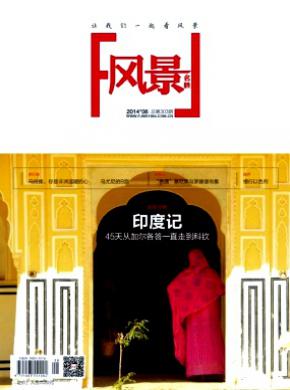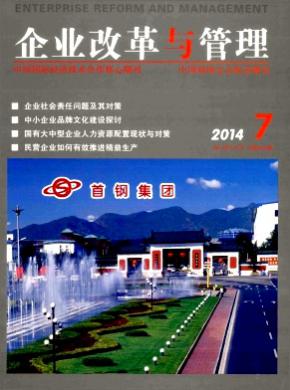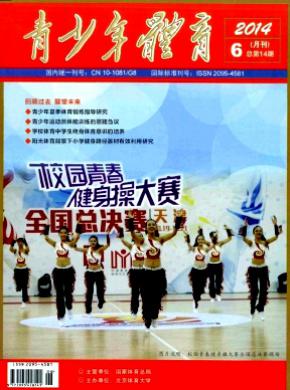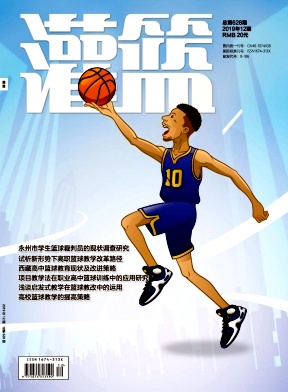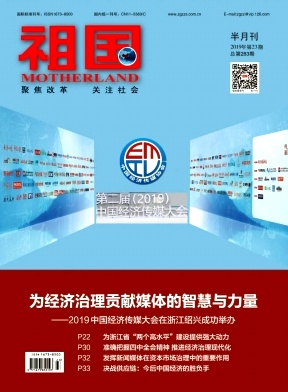如果地球上的生命始于星際物體墜毀在這里時呢?
上十月 19th, 2017,天文學家與Pan-STARRS調查首次探測到一個星際物體(ISO)穿過我們的太陽系。這個被稱為1I/2017 U1 Oumuamua的天體引發了重大的科學辯論,至今仍存在爭議。
所有人都同意的一件事是,對這個物體的探測表明ISO定期進入我們的太陽系。更重要的是,隨后的研究表明,有時,其中一些物體會以隕石的形式來到地球并撞擊表面。
這就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ISO已經來到地球數十億年了,那么它們會帶來生命的成分嗎?
在一個最近的論文,一組研究人員考慮了 ISO 對泛種癥的影響——泛種癥是生命種子存在于整個宇宙中并由小行星、彗星和其他天體分布的理論。
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ISO有可能在整個銀河系中播種數十萬(或數十億)類地行星。
該團隊由David Cao領導,他是托馬斯杰斐遜科技高中(TJSST)。與他一起參加的有彼得·普拉夫昌喬治梅森大學(GMU)物理學和天文學副教授,梅森天文臺臺長,以及邁克爾·薩默斯,GMU天體物理學和行星科學教授。
他們的論文,”'oumuamua對泛種癥的影響“最近出現在網上,正在由美國天文學會(AAS)審查出版。
簡而言之,泛種論是一種理論,即生命是由來自星際介質(ISM)的物體引入地球的。根據這一理論,這種生命以極端微生物的形式出現,能夠在惡劣的太空條件下生存。
通過這個過程,當物體通過ISM時,生命分布在整個宇宙中,直到它們到達并撞擊潛在的宜居行星。這使得泛種論與關于地球上生命如何開始(又名非生物發生)的競爭理論有很大不同,其中最廣泛接受的是RNA世界假說.
該假說指出,RNA在進化中先于DNA和蛋白質,最終導致了地球上的第一個生命(即本土出現)。
但正如曹通過電子郵件告訴《今日宇宙》的那樣,泛種癥很難評估:
“泛種癥很難評估,因為它需要納入許多不同的因素,其中許多因素是不受約束和未知的。例如,我們必須考慮泛種論背后的物理學(在最早的生命化石證據出現之前,有多少物體與地球相撞?),生物學因素(極端微生物能忍受超新星伽馬輻射嗎?)等等。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還有一些我們還沒有答案的問題,或者我們無法有效地建模,例如,即使一個有生命的物體與地球相撞,實際到達地球的極端微生物的數量,以及生命實際上可以從外來極端微生物開始的概率。這些因素的集合,以及更多因素的收集,例如不斷變化的恒星形成率和最近探測到的幾顆流氓自由漂浮的行星,使泛種論難以評估,因此,我們對泛種論合理性的理解在不斷變化。
2017年對'Oumuamua的探測構成了天文學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因為這是第一次觀測到ISO。
檢測到它的事實表明這些物體是具有統計學意義在宇宙中,ISO 可能定期穿過太陽系(其中一些可能仍然在這里).
兩年后,第二個ISO被探測到進入太陽系(2I/鮑里索夫),只是這次它的性質并不神秘。當它接近我們的太陽時,2I/Borisov形成了一條尾巴,表明它是一顆彗星。
隨后的研究表明,其中一些物體變成撞擊地球表面的隕石,甚至已經確定了一些。這包括中國國際石油公司 2014-01-08,一顆流星撞上了2014年的太平洋(并且是伽利略項目).
正如曹所解釋的那樣,發現這些星際訪客也對泛種論和正在進行的關于地球生命起源的爭論產生了影響:
“Oumuamua是泛種論模型的一個新數據點,因為我們可以使用它的物理特性,特別是它的質量、大小(球面半徑)和隱含的ISM數密度,來模擬星際介質中物體的數量密度和質量密度。這些模型使我們能夠估計星際介質中物體的通量密度和質量通量,并且通過這些模型,我們可以近似計算出在8億年內撞擊地球的物體總數(這是地球形成和最早的生命證據之間的假設時間段)。
“了解在這8億年期間地球上的碰撞事件總數對于泛種論至關重要,因為在此期間與星際物體的碰撞事件數量越多,泛種論的可能性就越高。
“簡而言之,星際'Oumuamua'的物理特性允許創建確定泛種論合理性的數學模型。
除了考慮泛種論背后的物理原理的數學模型(即數量密度、質量密度、總撞擊事件等)之外,Cao和他的同事們還應用了生物模型這描述了保護極端微生物免受天體物理事件(超新星、伽馬射線暴、大小行星撞擊、路過的恒星等)。
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討論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宇宙射線侵蝕了除最大ISO之外的所有 ISO在他們到達另一個系統之前。
這些額外的考慮因素最終會影響將影響地球的物體數量(未被天體物理來源消毒)和泛種論的合理性。
“為了得出最小物體尺寸,我們應用了各種模型,例如,球體堆積法粗略估計噴射物到最近的超新星祖先的距離(使用獵戶座A,一個致密的星團,作為我們的模型),到達噴射物的伽馬輻射,以及衰減系數(噴射物吸收的輻射量)基于噴射物(水冰)最可能的化學成分。“曹說。
根據他們結合的物理和生物模型,該團隊得出了在生命出現之前撞擊地球的噴射物數量的估計值。根據在澳大利亞西部發現的最古老的化石證據(來自可追溯到太古宙的巖石),最早的生命形式出現在大約 35 億年前。曹說: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泛種論引發地球上生命的最大概率是10-5的數量級,即0.001%。雖然這種可能性看起來很低,但在最樂觀的條件下,我們的銀河系中可能存在4×109顆宜居帶系外行星,這可能表明總共有104個宜居世界孕育著生命。
“此外,我們將我們的分析限制在地球歷史的前8億年,在最早的生命化石證據出現之前,但由于生命可以在行星生命周期的任何時候播種,而且行星的宜居壽命要長得多(高達5-100億年),我們將對銀河系中擁有生命的宜居世界總數的估計提高了一個數量級。
由此,曹和他的同事們得到了大約105顆宜居行星的最終結果,這些行星可以在我們的銀河系中孕育生命。然而,這些估計是基于對行星宜居性最樂觀的預測。
換句話說,它假設所有在宜居帶內運行的地球大小的巖石行星都能夠支持生命,這意味著它們的表面有厚厚的大氣層、磁場、液態水,并且所有幸存下來的生命噴射物都能夠將微生物沉積在表面。
正如曹總結的那樣,他們的研究結果并不能證明泛種論,也不能解決關于地球上生命起源的爭論。然而,它們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和限制,說明生命通過像“Oumuamua”這樣的物體來到這里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這些發現可能會對天體生物學產生重大影響,天體生物學正成為一個日益多樣化的領域:
“我們將物理學、生物學和化學納入研究作為生命起源的泛種論,在一個研究領域擁有如此多樣化的主題是很少見的。我認為天體生物學正朝著更加跨學科的方向發展,我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趨勢,因為它將允許所有背景的專家推進天體生物學。
“我們的研究可能有助于這一趨勢。就我們對泛種論的發現而言,泛種論引發地球上生命的可能性不大,但銀河系中孕育生命的宜居帶行星的數量要大得多。
“未來的天體生物學研究可能會利用這些發現來建立我們對泛種論的研究。然而,我們并沒有納入甚至不知道所有可能影響泛種論合理性的因素。
“我相信我們的研究結果為未來的泛種論研究開辟了新的研究方向,通過更新我們的模型或納入其他因素來建立。
“如果我們確實在未來發現其他星球上存在生命的證據,無論是在我們的太陽系中還是通過系外行星大氣中的生物特征,一個潛在的研究領域是考慮實驗和觀察測試,以區分通過泛種機制到達的生命或獨立進化和產生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