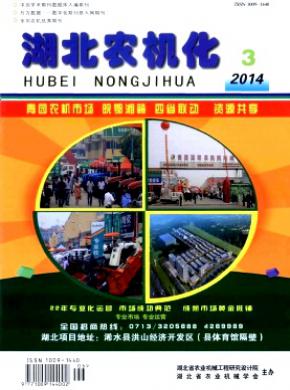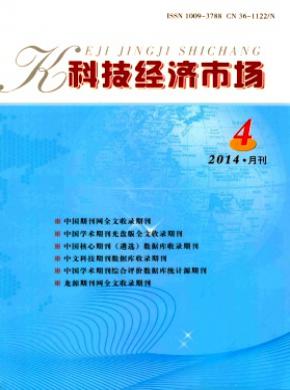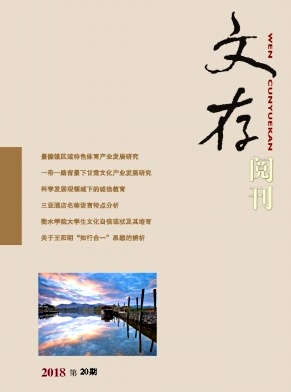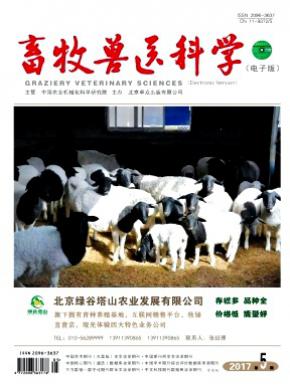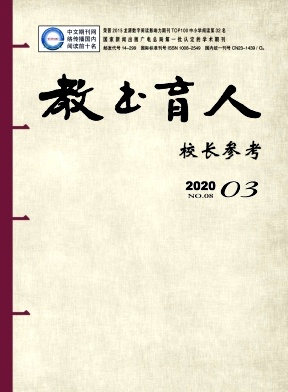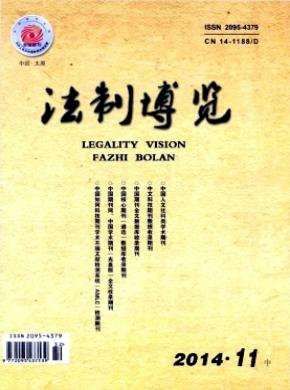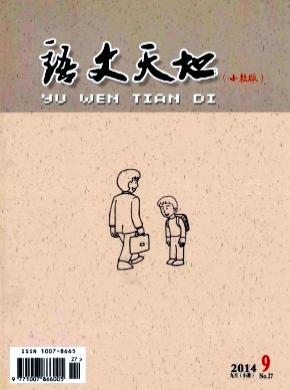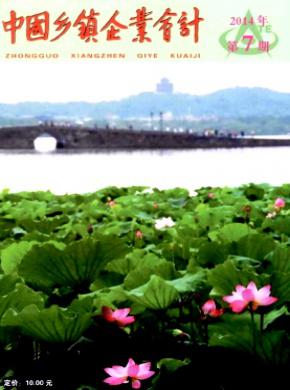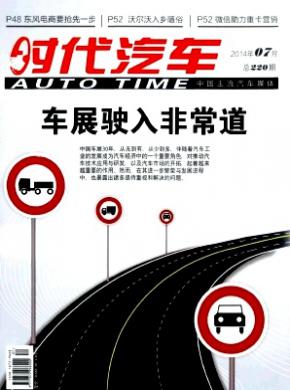對 6,000 次掃描的研究揭示了與 ADHD 癥狀相關的全腦模式
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已經確定了與以下癥狀相關的大腦連接的特定模式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多動癥),強調了在理解疾病性質時考慮各種神經功能的重要性。
雖然研究是遠非獨一無二在試圖識別大腦線路中ADHD的物理特征時,其方法確實旨在改進過去的努力。
美國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新技術,可以分析大約6000名兒童的腦部掃描,從而提供廣泛的大腦視圖,解決了過去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
“ADHD的神經影像學研究受到樣本量小、影響小和研究方法差異的阻礙,”寫來自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生物信息學家Michael Mooney及其同事在他們發表的論文中。
使用所謂的多神經風險評分(PNRS)將微小的差異組合成全腦連接模式,研究人員可以預測兩個獨立隊列中的ADHD癥狀。這些發現可能有助于未來對這種疾病的研究,并指出一種研究其他神經系統疾病中腦成像的新方法。
多動癥是一種復雜的神經系統疾病這影響了數百萬人兒童數量和成人.其診斷主要基于行為,通常表現為注意力不集中、沖動,有時還表現為多動癥。
ADHD的早期診斷可以對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產生重大的有益影響。一項研究發現,那些直到成年才被診斷出來的人早逝的可能性高出四倍比一般人群。
這種疾病是經常被污名化,有時歸因于懶惰或缺乏自制力。然而,研究表明,多動癥源于大腦在結構水平上功能的差異。這些結構差異的確切性質和程度尚不清楚,可能是因為對大腦特定部位的影響很小,這使得識別單個神經特征成為一項挑戰。
多動癥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現不同,這可能與不同功能的大腦系統如何相互作用有關。功能網絡之間的這種連接可以通過大腦中血流的變化來衡量,而它并不專注于一項任務——靜息態功能連接 MRI(rs-fcMRI)。
一個2014年回顧對 ADHD 的 rs-fcMRI 研究顯示,關于大腦默認模式網絡的發現存在一些一致性。最近薈萃分析表明多個大腦網絡中的連通性與ADHD有關;然而,大多數研究都沒有關注全腦效應。
“鑒于大量證據表明ADHD與廣泛分布的大腦網絡的改變有關,以及單個大腦特征的微小影響,因此有必要從全腦角度關注累積效應,”該團隊寫.
研究人員構建并驗證了PNRS,以代表與ADHD癥狀相關的靜息態功能連接的全腦測量的累積總效應。
他們使用了來自 rs-fcMRI 掃描和 5,543 名參與者的 ADHD 癥狀評分的數據;9-10 歲的兒童在注冊時青少年大腦認知發展研究,這是一項關于成年期大腦發育的長期美國研究。
然后對來自 PNRS 和 ADHD 癥狀的 553 名參與者進一步測試了俄勒岡州 ADHD-1000 隊列,一個獨立的數據集,由基線時年齡在 7 至 11 歲之間的人組成,他們每年都會進行隨訪測試,直到成年期。
“ADHD PRNS”與兩組的ADHD癥狀顯著相關。在俄勒岡州組中,ADHD PRNS 最高的 10% 的人被診斷為 ADHD 的可能性是低于中位數的人的 3.86 倍。
當對 1.83 年后進行第二次掃描的患者重復分析時,PRNS 和 ADHD 之間聯系的強度幾乎完全相同。
與ADHD最重要的關聯分布在多個大腦網絡中。最強的影響與大腦休息時最活躍的區域有關,稱為默認模式網絡;以及一種稱為 cingulo-opercular 網絡的結構,其中包括涉及認知控制、注意力和任務監控的區域。
PNRS與多基因風險評分不匹配,多基因風險評分表明一個人患有ADHD的遺傳可能性,這表明環境影響也有貢獻。Mooney及其團隊得出結論,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確定基因,環境和大腦連接如何相互作用導致ADHD。
也就是說,PNRS可能是ADHD的有用預測指標,并可能揭示與其他疾病的聯系,如抑郁癥.通過將其與其他因素相結合,我們可能會獲得對神經行為障礙的寶貴見解。
“這些發現強調了檢查累積的全腦效應的方法的前景,以及使用大樣本提高神經影像學研究的可重復性的重要性,”作者寫.
該研究已發表在神經科學雜志.